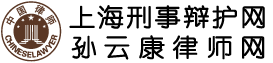有感于被害人(亲属)影响司法
最高检察院通报一起经最高检抗诉纠正的故意杀人申诉案,被告人辛某和被告人张某某曾为男女朋友关系,辛某不满张某某终止恋爱关系,反复纠缠骚扰威胁无果后,持刀上门将张杀害,辛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审法院判死缓,辛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未排除合理怀疑,定案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为,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法院重审后改判辛某无罪,驳回被害人亲属附带民事赔偿诉讼,检方不服,向高级法院提出抗诉,省检察院以下级检察抗诉不当为由,决定撤回抗诉,省高院同意了省检撤回抗诉申请,辛某无罪判决案生效,辛某获得了国家赔偿。
2018年11月,被害人亲属张某向省检提起申诉,请求撤销省检察院作出的撤回抗诉决定,对辛某无罪判决案提出抗诉,省检察受理复查后决定不予抗诉。
2020年1月,张某向最高检申诉,同年11月,最高检决定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无罪判决错误,后组织专家论证,一致认为无罪判决错误,最高检决定立案复查。承办人自行补充侦查,开展系列调查取证工作,经大量调查取证后,最高检认为应对辛某无罪判决提出抗诉,经检委会讨论后,2022年2月,最高检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6月,最高法院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同年12月,法院判决辛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
现实司法实践中,纠正有罪判决、改判无罪案例不少,纠正无罪判决、改判有罪的案例罕有,体现出司法的成熟和进步,最高检察院有错必究的态度值得肯定,尤其是富有公义责任感的最高检察院申诉复查检察官,希望只是好的开始。
刑事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享有程序制约权利,对刑事裁判发挥着影响力,辛某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亲属执着追求司法正义,这才有了抗诉程序的启动,错误裁判的纠正。笔者注意自媒体披露四川高级法院审理的屈某故意杀人罪二审改判案,被害人亲属同样发挥了司法纠错正向力量。
被告人屈某和被害人顾某某(女)曾为男女朋友关系,交往过程中,顾发现屈品行不良,存在欺骗,遂提出分手,屈不同意,反复纠缠,软硬兼施,发展到携带刀具上门打闹威胁。最终,顾某某上门持刀杀害顾某某,作案手段极其残忍,面对顾某某女儿,疯狂捅刺顾某某数十刀。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屈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犯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合并执行死缓,并限制减刑。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被害人顾某某亲属联名上书二审法院,坚决要求改判屈某死刑立即执行,最终,二审法院改判屈某死刑立即执行。
尽管屈某杀人起因和情感纠纷有关,但被害人顾某某并无过错,屈某实施杀人行为前,对顾某某长期骚扰,实施寻衅滋事,已构成犯罪。杀人行为凶残血腥,属蓄意杀人,并非冲动激情犯罪,一审法院机械适用被告人因感情纠葛杀人慎用死刑司法政策,二审改判屈某死刑立即执行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符合本案的实际。
故意杀人罪案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亲属的态度似乎决定着被告人能否“刀下留人”,如被害人亲属对复旦大学医学院林某某投毒案、上海朱某某杀妻冰柜藏尸案的刑事裁决影响明显。对民间纠纷、婚恋家庭矛盾引发的杀人犯罪,少杀、慎杀有明确的司法政策要求,刑事司法从不愿公开确认当事人具有影响司法裁决的力量,但实践规则中已有显现,如被害人谅解、和解制度规则,林某某、朱某某杀人案中,被告人若能取得被害人亲属出具的刑事谅解,至少笔者想象两位被告人可能保全性命,尤其是高校学生林某某。现实是,被害人亲属不接受赔偿不愿谅解,坚持要求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外加社会舆情对被告人不利,司法天平倒向一杀了之不足为过。
基于刑辩律师的观察和立场,被告人,被害人都是刑事委托法律服务主体,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都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履行实现法律公义的角色,大多情形下,两方刑事诉讼主体利益会有冲突,就被害人诉讼立场,刑事个案中,被害人(亲属)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力并非都是正向积极,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案例即有要求具体司法裁决时排除被害人不当干扰、严格执法。刑事诉讼为各方当事人参与司法过程,力量均衡、利益兼顾是公义裁判之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