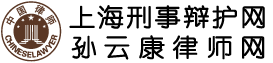深圳鹦鹉案辩护要点管见
深圳鹦鹉案辩护要点管见
孙云康
一、案情简介
近日,深圳宝安区法院的一则刑事判决成为网络舆论场热点,据网上披露的案情,王鹏自2014年4月起,以出售牟利为目的,开始驯养国家保护品种的鹦鹉。案发系公安机关查获鹦鹉收购人谢某某,该嫌疑人交代王鹏向其出售六只鹦鹉,其中两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绿颊锥尾鹦鹉。另外,公安机关查获王鹏饲养,尚未出售的45只鹦鹉也属禁止买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未出售被查获,属犯罪未遂。法院认定被告人王鹏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该案经被告人亲属网络公开喊冤,引发社会关注和各方争议,已有律师表示愿介入二审无罪辩护意愿。主要观点有:1、案件涉及大量类似的动物养殖者和使用者,认定犯罪超乎想象,司法不能脱离人性。2、王鹏人工繁殖饲养的鹦鹉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鹦鹉的行为无罪;查获的45只鹦鹉“待售”并无事实依据。3、王鹏扩大了鹦鹉的规模,养鹦鹉是宠爱,不会损害鹦鹉的生存环境,反而有利于法律本身的目的。
上述无罪辩护观点一经披露,随即遭到反对者批驳,他们认为:法院并未认定王鹏养鹦鹉有罪,而是制裁非法出售牟利行为,被告人出售的两只珍贵、濒危鹦鹉品种踩了刑法红线。查获的45只禁止买卖的鹦鹉认定犯罪未遂,也有事实依据,被告人在2014年4月开始饲养鹦鹉,出售其中六只,饲养目的为出售牟利可以证实。王鹏被认定犯罪获刑五年,对照法律规定并不冤。
二、一审的法律适用
本案法律适用涉及我国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相关司法解释为200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解释”第三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一)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严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一)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特别严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此外,根据“解释”附表: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量认定标准,涉及鹦鹉类数量标准为:六只为情节严重,十只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非法出售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绿颊锥尾鹦鹉两只,另有45只受保护鹦鹉属于犯罪未遂,本案涉及同一案中,被告人犯罪行为既有既遂,也有未遂情况下,如何量刑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62号(王新民合同诈骗案)中确定的量刑原则,在数额犯中,犯罪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分别对应不同法定刑幅度的,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本案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对应不同的鹦鹉数量,据此对应不同的量刑标准,出售未遂45只鹦鹉部分对应的刑期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既遂两只部分对应的刑期为五年以下。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清处罚。一审法院判处王鹏有期徒刑五年,应该是对未遂部分适用的量刑幅度适用了减轻处罚,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由于既遂部分量刑标准低于未遂部分,法院适用处罚较重量刑幅度,判五年有期徒刑,从法律适用上观察,尚未从轻处罚。
三、本案辩护要点探析
结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被告人王鹏饲养受保护鹦鹉品种,并出售牟利,是否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构成犯罪?显然,认为驯养保护动物不属于刑法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观点缺乏法律支撑,“解释”已明确将“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涵盖在内,即便行为人出售的是经驯养繁殖的珍稀保护动物,仍有犯罪可能。例如,野生东北虎属于受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动物园中驯养繁殖的圈养虎仍然受到法律保护,即便其死亡,虎制品也不允许被随意处置。至于私自饲养繁殖野生保护动物行为有利于种群扩大,不会破坏其野外生存环境的观点也无法立足,刑法所以将“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纳入保护范围,为从源头保护野外种群的根本目的。就被告人王鹏非法出售鹦鹉案,一审法院将其出售人工驯养繁殖鹦鹉行为认定为犯罪,法律适用上似乎并无瑕疵。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鹦鹉案的刑事辩护已无路可走,无策可寻?至少,笔者不这样认为,从网络披露的案情观察,本案似乎存在无罪辩、罪轻辩护两种可能性。首先,关于无罪辩的观察:近年来,国家对环境资源保护宣传和投入力度不断强化,对于破坏环境,非法狩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各类犯罪行为得到初步遏制,同时,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提高。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新情况,表现为,长期以来,社会公众缺乏对保护环境资源重要性的认知,行为人对收购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性质缺乏正确认知,不知不觉中触犯刑律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体现在象牙、犀牛角制品的民间交易行为,鉴于两类珍贵、濒危动物制品属于文化传承的手工艺品,历史上就有民众收藏、鉴赏传统,事实上,普通公众有可能对象牙、犀牛角制品被刑法禁止交易的规定不了解,不明知,交易则入罪,容易激发社会矛盾,也不符合公众对法律的公义认识。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含义和收购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并作出如下解释: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
依照上述立法解释,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的犯罪构成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应具有对收购物违法性之明知,包括知道或应当知道,若行为人不明知收购物为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收购行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立法解释仅仅对下游的收购行为入罪规定了主观明知条件,对同一条款中的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是否需要知道或应当知道出售的野生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没有明确规定。笔者以为,既然收购行为人不明知便无法定罪,出售人不明知却构成犯罪,两者失衡缺乏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及公平性。道理也是简明的,并非所有动物及其制品都禁止出售,当行为人对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性缺少明知的状况下,对出售行为客观入罪有违法律正义。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国家通过加大法制宣传广度和深度,教育及培育公民守法意识为正确路径,近年来,体育明星姚明担任形象大使的公益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深入人心,公众已逐步意识到非法买卖象牙,犀牛角制品的违法性,并以自身行动抵制非法买卖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涉及深圳鹦鹉案,笔者观察网络公开被告人王鹏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语句:“不过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这种鹦鹉触犯法律。”。笔者无法阅看到案卷材料,无法确证被告人对出售鹦鹉品种违法性不明知的辩解是否有充分证据支撑。被告人王鹏驯养出售的鹦鹉存在非保护品种,司法机关须查证被告人有否对不同种类鹦鹉法律保护范围的认知水平,假如无有证据证实王鹏对出售的绿颊锥尾鹦鹉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品种具有认知,根据上述立法解释精神,法院不能认定其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根据网上公布的案情,收购者谢某某被认定犯有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想必有充分证据证实该行为人对于收购的绿颊锥尾鹦鹉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品种,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便如此,并不能以收购人的明知推断出售人的明知。对于公安机关查获的未出售的45只鹦鹉,被告人王鹏主观上是否明知为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案件事实,司法机关也必须要有证据加以证明,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能追究刑责。
其次,本案罪轻辩护的途径:一审法院认定公安机关查获被告人王鹏驯养的45只国家保护的鹦鹉,被告人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未遂),此认定直接决定了被告人刑罚量,也决定无法适用缓刑处罚。据报道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4月,被告人王鹏开始非法饲养、繁殖珍贵、濒危鹦鹉并将之出售而进行牟利,2016年4月初,将两只珍贵、濒危鹦鹉以每只500元价格出售给谢某某,,,,,,”。被告人卖两只珍贵、濒危鹦鹉给谢某某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另还查获45只列入公约附录二的被保护鹦鹉待售,属犯罪未遂。法院认定的“待售”事实在犯罪形态上如何认定?涉及到犯罪预备、还是犯罪未遂的法律适用。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鹏饲养、繁殖的被查获的45只鹦鹉,在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形态上,是属于预备还是未遂?王鹏饲养、繁殖鹦鹉目的为出售,该事实认定当无疑问,从数量观察,远超家庭宠物合理范围,且行为人存在出售的客观行为。从形态观察,该阶段符合为犯罪制造条件的预备阶段的特征,饲养、繁殖45只鹦鹉,是为出售作必要物质准备,包括孵化,饲养、繁殖过程。犯罪未遂的要求,行为人要符合着手实行犯罪,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刑法并未将饲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规定为犯罪,孵化,饲养、繁殖等过程行为就无法被认定为着手实施犯罪,刑法理论中的着手实施犯罪,简单说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超出犯罪预备阶段,进入到具体犯罪实行阶段,即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实行行为,而预备行为仅仅为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本身对客体不能造成侵害,犯罪未遂中的实行行为是在预备基础上实施真正的犯罪行为,该行为能使客体遭受直接侵害或直接威胁。具体到鹦鹉案,被告人王鹏饲养繁殖的45只鹦鹉被侦查机关查获时,如若司法机关并无证据证实王鹏已实施联络买家,着手实施出售,依法不能认定被告人王鹏已着手实施非法出售的犯罪行为,饲养繁殖过程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王鹏即便有非法出售牟利的计划,但尚未有实际出售行动发生即被查获,不符合刑法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仅属于犯罪预备。
被告人王鹏被查获的45只养殖鹦鹉如能被法院认定为犯罪预备,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最轻可处免除处罚,实际出售的两只绿颊锥尾鹦鹉,量刑幅度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考虑到具体案情及社会效果,在具体量刑上,法院依法可对被告人王鹏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